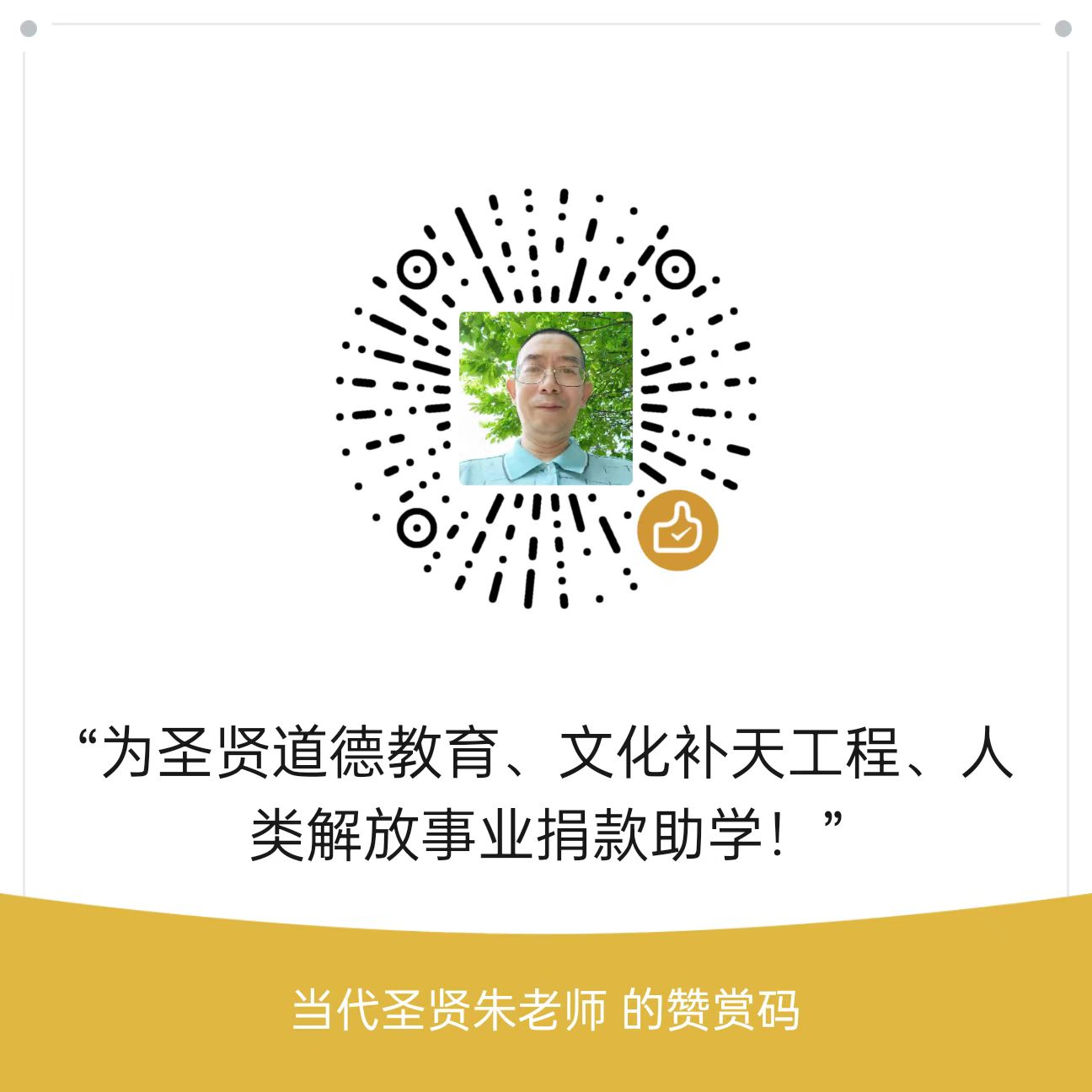回顾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注:原文段落较长,为方便读者阅读思考,文中小标题为朱老师所加。
作者:卢之超 来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
这是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思想界展开的一场重大的理论性和现实政治性的争论。争论一方面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关系如何认识和推进我们正在进行的实践,应该说是严肃的和具有原则性的。但不幸的是,这场争论虎头蛇尾,留下的是更多的分歧。
参加争论的两位主要人物,周扬同志和乔木同志,都是我尊敬的前辈。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我有不少时间在乔木领导下做点具体工作,同他比较熟悉。过去只是同周扬住在一个办公大院里,听过他的报告,参加过他主持的一些会,没有工作上的接触,他并不认识我;后来在理论务虚会上他是我们的组长,我的一些发言可能引起他的注意,才大概对我有个印象,以后又没有多少接触。他们两位虽然个性很不一样,但都是忠诚党的事业而且思想非常深刻的人物,都是具有矛盾性格和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而且两位都已相继离开了我们。
虽然由于工作关系,我了解这一争论全过程中一个重要方面的大部分情况,某种程度上说也参与了争论。但是要真正动手写这篇回忆性的叙述,仍感到十分为难。只是近来出现了不少与这场争论有关的记述和评说,叙说迥异。有些貌似亲历的叙述,实际离事实甚远。有人情况了解得很少,结论却下得十分大胆。因而不得不说明一些我所了解的情况。
对于这场争论,我当然有自己的观点。这里主要不是谈理论观点,而是想根据亲见亲闻和亲身经历,从我所了解的角度,谈一些实际过程。观点可以继续争论,事实却是客观的历史存在,容不得臆想和编造。
一、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性讨论
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学术性讨论,三中全会以后不久便开始了。
作为对过去左倾思潮下全盘否定人道主义的种种错误观点的拨乱反正,作为对“文化大革命”中种种非人道罪行的清算,思想解放之初,重提人道主义问题是很自然的。据统计,到1983年,有关的讨论文章至少已有四五百篇,我印象中就有邢贲思的《怎样识别人道主义》、汝信的《人道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吗?》和王若水的《人是马克思的出发点》等文章。还开过一些学术讨论会、出过一些文集。
我在1982年2月就参加过一个讨论会,那是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名义召开的,邢贲思主持。记得他在开场白里说,于光远曾找他谈,说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移,我们应当向前看,研究经济规律这些问题。现在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很热烈,这种讨论有什么意思呀?邢说我不同意于光远的看法,人道主义还是很值得讨论的。于是讲了很多要讨论的道理。
我当时还没有到中宣部,对问题和讨论的背景都不大清楚,是个旁观者和学习者,觉得于光远讲得有道理,理论界的精力主要应该放在现实问题上;又觉得人道主义是个学术问题,讨论讨论也很好。这个学术讨论会在全总干校开了两三天,各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大部分都到了。这些情况说明,在当时,尽管学术观点上分歧很大,甚至针锋相对,但是都属于正常的学术理论讨论。本文说的不是这种正常的学术讨论,而是那场政治理论性的争论。
争论是从周扬在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会上的报告引起的。这是由中宣部、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和教育部联合举办的报告会。
事先,中宣部请周扬作主要报告人,题目好像是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问题,并提议请几位专家帮助周扬起草报告稿。后来正式准备起草的时候,周扬改了题目,另组了班子,请了王若水、王元化、顾骧等几位,在天津帮助他起草。听说周扬在报告之前几天,曾给邓力群打电话,说他改了报告题目。那时我刚到中宣部理论局不久,不大了解这个纪念会的情况和准备过程。
大约在报告会前两天,顾骧从天津打电话到理论局,说周扬讲话要改个题目,不专讲文艺或文化问题,而是从广泛的角度讲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我虽然不知原委,觉得周扬是中宣部顾问,又是宣传部门的老领导,他决定这样改一下当然没有问题。理论局参与纪念会的一些具体筹备工作,只是要了解一下这个报告的准备情况和题目。
3月7日上午,纪念会在中央党校举行。周扬做了长篇报告,开场白以后请一位广播员念的稿子。讲话稿是《人民日报》排的清样稿,在会场上发给了一些人。我坐在下面听,觉得周的学识渊博,思想深刻,从认识论讲到辩证法,许多问题讲得很不错。但听着听着也产生了一些疑问,特别对有关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讲法,觉得问题比较大。
虽然对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自己一时也弄不大清楚,不敢下判断。但觉得在这样的场合,以周扬这样的身份,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就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是不大合适的。
报告受到鼓掌欢迎,但当场也有不少的不同意见,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我就听到了一些议论,后来又有各种渠道反映到邓力群、胡乔木那里。这天邓力群参加会了,也是在会场拿到稿子的。胡乔木没有到会,下午他参加了纪念马克思展览会的预展。我问他的秘书,乔木事先知道不知道周讲话的内容?秘书说肯定不知道,他上午才收到讲话的清样稿。
我说了我的一点看法,请他快向乔木报告。
后来我看到,周在送这个稿子时有个便条:“乔木同志:送上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学术会上讲稿,请你详加阅改退下。我病后初愈,过些时当来看您。敬礼,周扬,三月七日。”第二天(即3月8日),《人民日报》没有用新华社发的新闻稿,独家发表了周扬讲话的详细报道,并预告说“全文本报另行发表”。
果然,乔木看了稿子和报道,也听到一些反映,认为问题不小。
8日下午,邓力群从医院出来(他当时正住院检查)向我们布置说:经与乔木商定,这个纪念会要延期两天。既然有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可以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大会发言,把这个会开成学术讨论会,有各种意见,各种声音。不然国内外会把周扬的讲话误解为代表中央的意见,而周的讲话内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观点并未报告中央同意。
于是让理论局迅速请一些人作大会发言,参加讨论。邓还说,明天(3月9日)中宣部要开领导小组会,传达乔木的意见。3月9日,我就去落实交给理论局的任务。
当时哲学界一些知名人士正在酒仙桥饭店开关于大百科哲学卷的会,我赶到那里分别同他们中一些人商量。本想请邢贲思在大会做个发言,忘了什么原因没有他。好在有不少人不同意周的观点,于是很快就约定了三位专家于3月12日在大会发言(他们是北京大学的黄楠森、社会科学院的王锐生、人民大学的靳辉明。另外还有一位在大会发言的是文艺界的唐达成)。这些发言既不是批评周的观点,也不可能要求都正确,只是要表明本来就存在的不同意见。
二、传统社会主义始终拒绝人道主义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的秦川曾打电话给邓力群,问是不是可以全文发表周扬讲话。邓没有把握,要他一定去请示胡乔木,根据乔木的意见再决定。与此同时,胡乔木于3月10日到周扬家,约集夏衍、王若水、郁文、贺敬之等五位同志谈他对周扬讲话的意见。
据我不久听到的传达和后来看到的材料,乔木同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对周十分尊重和客气,语气特别缓和,甚至过分委婉,但意思还是很清楚的。他说:
“周扬同志的这篇文章讲得比较周到,但有些问题还没有鲜明地讲出来,或者还讲得不够圆满,倘若就这个样子拿出去,可能产生一些误会。文章中有些话是不可取的。”
“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但是我看到周扬同志的文章,抽象化的议论比较多,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首先,人道主义最好加个限制词叫‘社会主义’,没有这个限制词,就可能混同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马克思主义成熟的标志,首先就在于它不再讲抽象的、孤立的人,主要是讲社会,转而认定人只能是社会的实践的人,解决人的问题不能离开社会,离开历史,这才是根本的变化。”
“因为从个人转到社会,这才发现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一系列的问题。”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来说,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的。这是资产阶级哲学家、思想家最流行的说法。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全世界人道主义者中恐怕占绝对优势。他们在魏京生等等这些事件上都是这么说的。我们提出人道主义究竟是讲什么东西,应给中国、外国一个明确的概念。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糊涂思想”。
在讲了历史上有各种人道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以及“不经过阶级斗争解决不了人道主义提出的问题”等等以后,乔木说:
“我们宣传人道主义时,没有讲清这方面的道理。将人道主义宣传变成摘引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来同人道主义联系,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观点,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历史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联系起来。”
“单讲人道主义,不加社会主义,便会同历史唯物主义发生矛盾”。“所以人道主义本身实际上有种种不同的立场。”
“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如果我们不这样看,这样宣传,那么对于有斗争历史的和有党性的党员,就会在感情上格格不入,好像我们斗争了几十年,都不是人道主义,反而成了反人道主义的。”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今天实现了社会主义,一下子在各方面都实现了合乎人性的生活。这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一样,首先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谈话中间乔木还比较尖锐地批评了王若水的观点。
他还分析和批评了与此相联系的文学方面的一些现象以及现代派的种种表现。后来他又说,“我们宣传人道主义,不能不指出有人借宣传人道主义、人性论之名,来反对社会主义。同一个概念可能得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
但是这次没有谈“异化”问题。(这天下午,他打电话给郁文,不久又打电话给周扬,谈了对“异化”问题的意见,说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对此说法是不一样的,把它不加区别地应用到社会主义是不对的。)
谈了对周扬讲话的意见后,乔木很客气地对周扬说:
“周扬同志你已年高德劭,年老体弱,是否可以‘宜将剩勇追穷寇’,将文章未涉及的地方或未说清的地方,索兴说清楚一些,然后再出单行本。”
“周扬同志在文艺界是很有影响的。周扬同志的文章发表出来也会影响很大的,因而希望周扬同志能够将论点搞得更完整一点,修改好了,再正式发表。”
临别时他还十分郑重地对周扬说:“今天的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我是同耀邦同志商量了的,他特别提出要我用他的名义希望你把文章修改好了再发表。”
过了几天,3月15日,邓力群在中宣部部务会上传达了这个谈话,并说乔木与周扬说了,周扬的文章由他自己修改后全文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文章摘要可与不同意见的几个发言摘要同时在报纸上发表。接着,邓找我们商量周的讲话摘要和其他几个发言摘要如何在报上发表的事。
中间,他又和周通电话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大意是邓说乔木建议你把文章改好后在《哲学研究》发表,问文章修改好了没有,周坚持全文在《人民日报》发表,也不愿再修改,说既然讲了就不想改了;邓于是请他明天来中宣部开会,集体商量一下。
周开头不肯来,说你们开会谈吧,我不来。周的态度很傲慢。邓火了,说你是老同志,长期做领导工作,处理过很多事情;你是中宣部的顾问,需要讨论的时候你又不来,对你这种态度我有意见。后来周答应明天来参加会。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在第二天(3月16日)突然全文刊登了周文。
邓力群得知后,立即打电话给秦川(《人民日报》总编辑)和王若水(《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说前几天明确告诉秦川周文如何发表事先要请示乔木,王若水又当面听到乔木同周扬的谈话,为什么不经请示,不听招呼,就擅自发表?批评他们严重违反组织纪律,要他们做检查。
(秦川第二天就送来检讨,说完全接受批评,未经请示就全文刊登周文确是一个组织性的错误。还说发表是他决定的,王若水因参与起草这个讲话,也欣然同意。王也写了检查,讲了一些过程、做了一些解释,说他听乔木同周扬的谈话没有发现有多大分歧,又说发表这篇文章他要负更多的责任,发表前是应该打招呼的。还说没想到事情会如此严重。)
后来,邓又找了贺敬之、李彦和我三个人,布置乔木建议向中央写报告的事,并讲了要写的大致内容,包括事情的起因、经过,说除了理论观点问题以外又涉及组织纪律错误,以及建议如何处理。我们按他的意见抓紧起草。草稿写好后,中宣部在3月19日开部务会讨论。
邓力群说,乔木16日给他打电话说,《人民日报》刊登周扬讲话全文的事不能马虎,建议中宣部向中央报告情况。邓还说:这件事我向陈云同志作了报告,乔木向小平同志作了报告,我们两人都向耀邦同志作了汇报。昨天书记处会后又向邓、陈、胡扼要报告了,他们都同意。报告写好后报书记处。
又说,给中央的报告,理应先给周扬看,考虑他身体不好,怕吵起来,与乔木商量,写好后先送书记处,等决定后再商量如何用适当方式跟周扬谈。
这个报告是中宣部上报中央书记处的。题目叫“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不听招呼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里边讲了事情的经过,胡乔木同周扬等人的谈话和对他的批评,《人民日报》负责人秦川、王若水不听招呼发表全文的责任等,报告里说:
“应该注意到,在人道主义、异化等问题上,有一些人近年来发表了许多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怪论,实际上成为当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核心之一。文艺界也有人宣传超阶级观点,反对阶级斗争的作品已经发表好几篇。他们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攻击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反人道的。港台反共报刊,都据此宣传我们自己承认我们的社会是‘非人’(异化)的。”
报告最后提出的处理意见是:人道主义作为学术问题仍可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希望周扬对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负责的表现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
三、人道主义从来不是资本主义专利
说到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当时的情况。周扬讲话后,国内外确实有不少反映。在国内,从周讲话那一天起,就受到不少人热烈欢迎。国外境外,也有不少人鼓掌欢呼。
日本《读卖新闻》在周的全文发表后立即发了题为《中国宣布恢复人道主义权威,周扬作了自我批评》的报道说:“周扬从代表党的立场承认了迄今为止左倾政策的错误,宣布恢复人道主义的权威。”“可以认为,今天恢复人道主义的权威反映了党中央的灵活姿态。”
香港一家反动报纸发表社论,引述周关于人道主义的话以后说:“所以实际上毛共已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彻头彻尾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周扬也承认了这一点。”
港刊《争鸣》载文说,“近几年来,人道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文化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一些文艺作品,也在力图从人道主义的立场来描述人性和社会。海外某些观察家认为,人道主义的理论正成为对抗‘正统理论’的一股强大力量。”“周扬首先批准了人道主义的合法席位”。
当时许多舆论表明,确实不少人认为周扬是代表党的立场讲话的,把这件事看成是中央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看成是中国指导理论的大转变。胡乔木对这种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他抓得很紧,不断打电话给邓力群和中宣部布置任务。邓力群可能认为自己对这样专门的哲学问题了解不深,独自的主张不多,但执行乔木的意见很积极、很坚决。(后来他执行邓小平的有关指示也是很积极、很坚决。)
他们一面批评周扬等人,特别对《人民日报》少数负责人的做法十分重视,要求严肃进行批评和处理。一面对外努力造成学术讨论空气,力图消除误解。除了前面说的延长会期、增加发言外,3月25日,邓力群还召集了理论界、学术界的大型会议,布置编辑资料,开展人道主义问题的研究讨论。
他说:“今天请同志们来开这个会,就是想共同商量一下,在我们的思想界、学术界,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异化等问题,作为一个学术问题、理论问题,怎么样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怎么样进行一种正常的讨论。”
从当时情况看,通过内外两方面的工作,事情本来是可以在不引起较大震动的情况下逐步解决的。但事实是矛盾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了。王若水掌握着《人民日报》,急于要把他的或他所热烈拥护的观点公布于世,秦川则全力支持。
而周扬确是年高德劭,除了“文化大革命”里大家一起挨批受难以外,以前一直是领导、批评别人,决定别人命运的,站在“左”的立场整过不少人;“文革”以后,大彻大悟,觉今是而昨非,又一直开风气之先,大力倡导解放思想,正在努力树立另一种形象,从没想到会遇到现在这样的局面。何况批评他的胡乔木30年代曾在他之下,邓力群就更不在话下了。另外他对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久有研究,结合对“文革”的反思,不论对错,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固定的观点,也难以改变。所以一时很难接受批评和意见。
中宣部的报告经3月19日部务会讨论修改后,于3月20日上报书记处。听邓力群说,只送书记处,没有送小平、陈云和政治局其他人。
过了一个多月,邓力群又找我们谈与这个稿子有关的问题。他说,这已是第三稿了,原来中央也已同意。后来耀邦同志说批评材料要同本人见面,核实事实。问题不在稿子本身,细节上可能有些不确切不一致,主要还是看法问题,看法上不一致。这时我才知道核对事实的事。
此前在中宣部会议室核对事实的会,我没有参加。据说那个会上吵得很厉害。乔木对周扬说,我本来跟你说好,作为学术文章,修改好在《哲学研究》上发表。我也是代表耀邦同你谈话的。周说,我没有听见代表耀邦这个话。
又说,你这个人的话,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我知道你讲的什么,我根本记不住。说着两人就争了起来。然后就问那天谈话有没有记录,郁文说,不仅有记录,而且有录音。
另外王若水不服,说周扬有主要责任,秦川是《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为什么不处分他们?邓力群说作为学术问题可以各抒己见,为什么又对我进行处理?秦川、周扬又把责任揽起来,不同意处分王若水,说主要责任在我们。总之吵了半天。
这里不能不提一下胡耀邦同志。看得出来,一方面他事事都同意胡乔木的,因为他不太懂理论,乔木又是政治局分管思想宣传的,向他报告了他不得不同意;另一方面他心里实际上又不赞成这样做,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特别不愿意批评和处理周扬、王若水等人,所以他提出要把材料同本人见面。
他的这种态度以后会看得更清楚。果然,经过本人核实后的报告再报上去以后,就再没有下文。(这个报告根据核实做了修改于4月下旬上报,后面还附了几个附件:乔木3月10日同周扬等的谈话记录,周扬给胡乔木、邓力群并胡耀邦的信,秦川和王若水的检查。)
从4月底到8月底,除了胡乔木还在不同场合坚持批评以外,一直没有听到什么动静。我想,肯定是上面意见不统一,事情僵在那里了。这可以算是第一阶段。当时中宣部理论局的事情很多,我就忙着《邓小平文选》的宣传等等工作去了。
相关链接:
回顾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1)
回顾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2)
回顾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3)
回顾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