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三次危机
〔德〕卡·考茨基
(1903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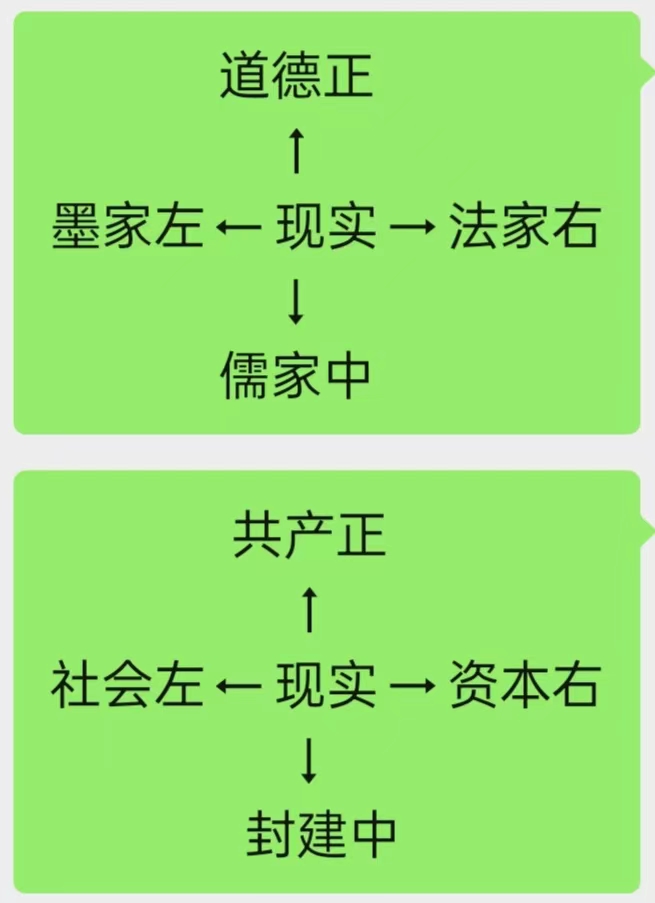
当卡尔·马克思1883年3月14日与世长辞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但是它还远没有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完全占据统治地位。在这之前的几年,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学说的理论影响和实践影响,经历了自己的第二次危机。第一次危机早在1848年反革命之后就已经出现。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继各次高潮时期之后,也曾经历过各次危机时期,而在克服危机之后,它总是赢得了新的基地。
在四十年代,在西欧开始了社会主义思想和工人阶级独立性迅速发展的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先进阶层的影响也有着迅速的增长。国际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在1847年完全站到了他们的基础上并且把《共产党宣言》作为自己的党纲。而当1848年爆发革命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成了德国革命者的主要机关报。
六月的大屠杀结束了这一上升时期,反革命获得了胜利。正如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一样,革命的失败也给予马克思主义特别沉重的打击。马克思主义不仅失去了在德国的政论性机关报,不仅它的组织在那里遭到警察和司法机关的致命打击,而且民主派也起来反对它,并且无论在德国或者在流亡中都不断地迫害它。
马克思轻蔑地摈弃了流亡者之间的无谓争吵,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高涨积聚新的武器,即使在最黑暗的反动岁月里,他也一刻没有怀疑过社会主义运动的新高涨。而这种新高涨在六十年代初来到了。于是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发展时期。
工人运动到处得到了比革命前更为广泛有力的开展,并且寻找进行活动的目标和手段,寻找启蒙和组织。马克思给了它二者。他并没有建立“国际”[指“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译者注],因为一般说来“国际”不是单独一个人建立起来的,但是马克思善于把汇集到他那里的各种不同的力量联合起来进行共同的事业,从而赋予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以力量,如果没有他,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就得不到这样的力量。而在建立“国际”后不多几年,他发表了《资本论》,从而把对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迄今所达到的最深刻的认识给了人类。
1864—1870年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是值得骄傲的年代。马克思主义重新从胜利走向胜利,并且愈来愈得到工人阶级的兴高采烈的信任,但也遭到统治阶级极端的仇视。
接着是巴黎公社的出现及其失败,这成了“国际”的转折点,就象六月大屠杀是1848年的民主派的转折点一样。这激起了统治阶级对于它所害怕的组织及其领导人的全部仇恨。而这些组织对于两倍和三倍的攻击的压力的回答,不是更加紧密地团结自己的队伍,而是比1849年以后民主派流亡者中间的纷争远为激烈和危险的分裂和内讧。
前面说过,马克思曾以高度的技巧和很大的宽容精神把形形色色的分子——罗曼语国家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英国的工联主义者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联合到“国际”中来,但是这种联合变得愈来愈困难了。1870年以前的国际的最后几次代表大会就已经暴露出严重的矛盾,尤其是在土地问题上,崇拜农民经济和土地私有制的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派,同那些主张用现代技术和现代知识的一切手段装备农业和实行土地公有制的人们发生了对立。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进展还把敌对的分子联合在一起。失败后的困难则引起了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分子的责难和敌视。
巴枯宁把这些人纠集在一起,当然并不是象马克思那样为了从事共同的建设性的活动,而是仅仅为了割断还把他们联结起来的一切纽带。巴枯宁得以破坏马克思的国际,但是他无法用另一个国际来取而代之。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之后国际瓦解了。
于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了自己的第二个衰落时期。在法国所有的工人运动都遭到镇压,在其他罗曼语国家里无政府主义猖獗,英国工联分子甘愿追随资产阶级政党,在德国,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还在互相斗争,在奥地利,运动从熊熊烈火变成了一小堆灰烬,其中少许火星还在发出微弱的闪光。
而他毕生的伟大著作《资本论》仍然遭到了忽视,马克思曾期待《资本论》会使人们的思想革命化。
因此,七十年代前期给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带来了许多失败,正如六十年代后期带来了许多成功一样。
走向新的高涨的转折这一次不再是来自法国或英国,而是来自德国。各地的独立工人运动由于公社的失败和国际的瓦解而遭到普遍衰落,而德国社会民主党则没有受到影响。187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赢得了辉煌的胜利,这一胜利在普鲁士引起了对它进行迫害的时期,但是这种迫害只是导致敌对的弟兄们联合起来(1875年)。从此以后我们党得到了几乎是不断的发展,甚至反社会党人法也只是暂时中断了这一发展。
不久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也开始传播并将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排除出去;1876年创办了《平等报》,由茹尔·盖得同拉法格、杰维尔和其他人一起编辑,而在1879年马赛代表大会上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党。
在比利时,工人们在七十年代后期也开始重新发动起来,即使不是在理论上,也是在实践上站到了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的立场上。1879年建立的比利时社会党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党,它致力于夺取政权,以解放劳动人民,而这就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与此同时,荷兰工人运动同样也从它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后陷入的沉睡中苏醒过来,阿姆斯特丹的“社会民主联盟”接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
丹麦在七十年代末同样也经历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显著高涨。
马克思在世时见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觉醒,同样也见到了使他特别高兴的俄国革命者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进行的反对专制制度的光辉的英勇斗争;他兴奋地注视着这一斗争,并且只要可能,就用忠告和通过个人的联系予以支持。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新觉醒,以及马克思给予这一运动的影响,终于打破了教授们用沉默来加以封锁的冰块。有人开始对《资本论》进行批判,并“通过科学的方式加以消灭”,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来使它为人们所知道并且对人们的思想发生影响了。随着它“遭到驳斥”,它的影响日益增长了。
但是,当马克思逝世的时候,终究还不能说,他的观点以及建立在这些观点基础上的实践已经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首先,罗曼语国家还严重地受到巴枯宁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侵袭,正当马克思逝世时,巴枯宁主义的一种形式还席卷着奥地利。
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领域当时比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还要狭窄。甚至在马克思的理论传播得最广泛的德国,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杜林,一个洛贝尔图斯和阿尔伯·朗格的观点,更不用说象约翰·雅科比和里廷豪森这些1848年的老人了。
当1877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始出版科学性机关报《未来》时,它不仅没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而且提出了一个直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而对此谁也没有提出抗议。当时用德语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另一个科学刊物(苏黎世的《新社会》)根本没有纲领。
但是突然一切都改观了。经过不到十年,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就占据了统治地位,正如各次国际代表大会(尤其是1893年的国际代表大会)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当时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出的热烈欢呼声不仅是对这位老战士个人的,也是对他所参与创立的学说的。马克思主义赢得了整个斯拉夫社会主义,它在罗曼语国家中有力地排挤了无政府主义;它在英国重新对工会发生影响,特别是对新的工联主义。
不仅实践马克思主义赢得了这样的统治地位,而且理论马克思主义也赢得了同样的统治地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消失了,现在只有一种学说——卡尔·马克思的学说有着重大意义。在八十年代初对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还有影响的理论家——蒲鲁东、洛贝尔图斯、杜林、朗格、亨利·乔治、谢夫莱对于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失去了任何重要的影响。在罗曼语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里,除了马克思主义外,以一种理论的姿态出现的还有马隆的“完整的”社会主义,它不再是一种独特的、严整的理论,而是从形形色色的体系——蒲鲁东主义、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和谢夫莱主义等等那里取来的片言只语的杂乱无章的混合物。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强有力的传播太迅速,太急剧,以致于它不可能持久。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的年青一代中成了时髦,谁不想被看作是“落后者”,谁就必须趋习这种时髦。但是再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不适合充当时髦哲学了,它是如此深刻,又是如此现实主义的,以致于它不允许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也不允许用玄奥的、神秘化的套语来回避对事物进行更深入的探究。为了理解马克思,必须要有一些知识,还要有一种不倦地不断深入探讨的渴望。在最初接触马克思的时候,人们对他的理解往往是很肤浅的和庸俗的。谁想理解他并且解决事物的外表及其本质之间、它的虚假的外表上的联系及其真实的深刻的联系之间的矛盾,他就必须经常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并且用新获得的认识经常重新研究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如同任何一种深刻的哲学一样,人们必须通过努力才能达到。时髦的人对此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些肤浅的公式,而这些公式使他们很容易同现实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毫不奇怪,他们把这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并且很快就修正自己的观点,但并不是对这些观点作更深入的探讨,而是撇开整个学说转到当前的问题上去。他们没有觉察到,他们所批判或修正的思想,其实就是这些先生们自己过去的思想。
但是即使马克思的学说比较肤浅的话,一些追求时髦的分子脱离它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时髦的本质在于经常的变换。时髦的人希望引人注目,希望同广大群众迥然不同,当大家还依恋着过时的、陈旧的时髦时,他就已经热中于最新的时髦。当一种时髦广泛流行时,对于时髦的人来说正好是要变换它的时候。因此,许多年轻人喜欢扮演严格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角色,只要这样一来能在他们的同伴之间引起注意。但是,当这种马克思主义失去新奇的刺激时,他们就觉得,马克思主义似乎过时了,他们就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需要。
于是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近的、第三次危机,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次危机的结尾,但是这次危机基本上已得到克服。今天,在马克思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可以满意地指出,这次危机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损害,比前几次危机要小得多。
首先,这次危机几乎完全没有涉及主要之点——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而这是可以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前几次危机是重大的实践上的失败的结果;它们更多地涉及实践方面的运动,而不是理论方面的运动。与此相反,最近的这次危机是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完全的胜利进军中产生的。它没有任何外在的原因,如果不算第二位马克思主义之父的逝世的话。
有人也许会向我们指出法国和意大利,似乎在这些国家中实践马克思主义正走向衰落。但是,那里的脱离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分子几乎都只是那些不久前刚加入的分子。甚至连那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中拥护阶级合作的人也还不敢公开地断然地放弃阶级斗争。他们没有坚决用另一种策略来反对阶级斗争的策略,而只满足于要求发表意见的自由和自治,他们的这些漂亮词句意味着取消任何党的纪律。但是除此以外在那些国家中还有一支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基本队伍,它的力量和团结同1893年相比宁可说是增强了,至少是没有遭到削弱。
如果说在法国和意大利有着相对的倒退,那么在其他国家则有着重大的进展。在荷兰,十年前还如此严重的无政府主义危机现在被完全克服了,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发展壮大。在美国终于产生了一个真正的美国社会民主党,它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此外还有俄国,那里的运动在1893年还完全停滞不前,而现在那里的年轻的无产阶级有力地行动起来,而且几乎完全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
但是,正如马克思的一句名言中所说的那样,一步实际行动比一百个纲领更重要。
然而,甚至连马克思主义的最近一次危机迄今也没有导致根本修改我们的纲领,只有法国除外,那里的内阁社会主义在自己的纲领中把社会主义运动说成既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又是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的产物,既是自由主义的对立物,又是自由主义的结果。
这个特殊的纲领所依据的理论是不存在的。一般说来马克思主义最近的危机没有形成任何可以同马克思主义相抗衡的理论。尽管有一切批评和指责,目前同十年前一样,马克思主义是唯一完整的、周密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逝世时还流行的其他一切理论已经被人忘记,但还没有产生一种新的理论。甚至刚刚出现的大卫的尝试也不是新的社会理论,而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即农业的新理论,他机械地把农业同整个社会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就工业而言,大卫承认马克思主义,就农业而言,他是一种新蒲鲁东主义者。他自以为他是在运用马克思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在另一场合详细谈到这种尝试。
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修正主义既不是它的继续发展,也不是以另一种学说来代替它;实际上,修正主义意味着不仅放弃马克思的理论,而且放弃一切社会理论;它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象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古典经济学家的关系一样。
当李嘉图学派瓦解的时候,代替它的不是一个新的更高的政治经济学体系,而是历史学派,这个学派把贫困说成是德行,而把对较深刻的经济联系的任何探求说成是一种空洞的思辨,只有当科学的事实材料还不够充分的时候,它才是合理的。在它看来,现在研究普遍的经济规律似乎有点过时了。经济生活过于错综复杂,以致无法把它置于普遍规律之下。组成现代经济科学的内容的,不是普遍的东西,而是特殊的东西,不是研究规律,而是描述发展和结果。这样一来,科学的先决条件在它看来就成了科学本身的总和。
当然,人们通过这种方式也可能对科学作出宝贵的贡献,历史学派曾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绩,特别是在科学史的领域里。但是也不应忘记,描述性的科学如果不想成为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细节性事实的简单堆积,就必须从一定的理论原则出发,它以这些理论原则为指导来挑选它所遇到的事实,把典型的事实加以突出和分类。例如,统计学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十分重要的结果,它使我们有可能比李嘉图和马克思更清楚地观察一些事物,而不管他们进行抽象的全部力量。但是一种有用的统计学的首要前提是合理地提出问题,而合理地提出问题又以对所研究的事物的本质有较深刻的理论认识为前提。
历史学派在自己的研究中如果不以伟大的经济理论家们的如此受到责难的抽象概念为指导(当然,往往是不自觉的),就不可能达到它已经达到的东西。另一方面也不应忘记,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即使不掌握现代统计学的成果,他们终究完全掌握当时的经济方面的事实材料。人们很容易忽略这一点,因为人们把他们的叙述方法同他们的研究方法混淆起来了。这种区别当然也已经“过时”了。我们现代的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克服者通常急于把每一个突然产生的想法和每一个观察立即写在纸上并且公诸于众,只是事后才去考虑,他们的伟大发现究竟有什么意义。研究的方法和阐述的方法在那里是一致的,如果还可以谈得上方法的话。如同许多现代商人把自己的全部货物陈列在橱窗里一样,许多现代经济学家把他们所掌握的全部事实材料写到他们的著作中去。至于根据浩瀚的事实材料可以作出一种抽象的阐述,在这些现代科学的代表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种抽象的阐述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臆想出来的阐述,一种没有根据的推论。
尽管历史学派对于李嘉图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退步,但是它仍旧能够用有价值的个别研究来丰富科学。同样,尽管修正主义对于马克思来说是一个理论上的退步,但是它仍旧能促进社会洞察力的发展,——只要它总算可以声称自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科学派别,而不是简单地恢复庸俗的感情社会主义的名誉。后者在七十年代在平庸的社会主义者中间还曾风行一时,后来就在马克思主义面前畏缩地隐匿起来,从而避免了被连根铲除,直到最近,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使它重新鼓起勇气来公开露面,并且把自己吹嘘成马克思主义的克服者。
如果修正主义认识到自己的能力的限度,并且象历史学派一样,把重点放在描述发展和结果上,那么,修正主义就能够作出有科学价值的成绩来。我们只须举出两个例子:韦伯夫妇以他们的《英国工联主义史》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以他的《俄国工厂史》作出了卓越的科学贡献,并且显著地扩大了我们的社会洞察力。
但是,当修正主义胆敢进入理论领域的时候,那么不管它是沿着批判的方向还是正面叙述的方向向前发展,它将经常遭到失败,因为它恰好不是新的、完整的和统一的理论,而只是对于今天唯一存在的社会主义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或歪曲。
但是,由于修正主义和历史学派不同,它不想立足于资产阶级的基础之上,而想立足于无产阶级的基础之上,所以,它一再被迫在理论领域中尝试一下,而这正是他最大的弱点之一。
一个上升的阶级在它所成长起来的那个社会的范围内不能达到完全的平等和自由的发展,一旦它在某种程度上有了自觉,就必然力求用另一个符合它的利益的社会形式来代替现存的社会形式。但是,如果它不制定一个关于整个社会的理论,它就不可能向自己提出这一目的。这个理论的性质取决于普遍的和它特殊的知识状况;有时它可能是很幼稚的并且满足于自己的历史作用,但是它必须始终同公认的科学观点相一致,并且必须包括社会全体。例如资产阶级,当它成为一个自觉的阶级并想根据自己的利益建立社会的时候,也需要一个广泛的社会理论,于是它在重农学派和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中得到了这样的理论。当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不再想改变整个社会,而是想保持它,只是在个别方面加以改善,这时,它对理论的需要也就消失了。
从那时起历史学派就成了它的科学需要的相应表现。历史学派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
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可能是经常的现象,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由于其阶级地位只能是偶然地、在特殊的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下得到实现,例如,在英国最近几十年中对于组织在工会中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来说,以及在1896—1900年期间对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无产阶级来说,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无产阶级在目前的社会中无法达到它所需要的社会自由和平等。因此,它通常必然对现存社会采取敌视的态度,必然力图改变整个社会,也就是说,它必然是一个革命的阶级。因此,无产阶级要求一个统一的广泛的整个社会的理论,以便可以根据这个理论来论证它的改造整个社会的意图。
过去,当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还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无产阶级可以从它那里获得自己的社会理论,使这种理论适应无产阶级的需要;而现在,只有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说,从无产阶级观点出发对社会的科学研究,才能提供革命无产阶级所需要的理论。
自从资产阶级变得保守以后,它已经失去了对于理论的需要,但是,这种需要在无产阶级中间却由于它的阶级地位而不断重新产生。因此,无产阶级已经不能长久地满足于象修正主义所做的那样,把历史学派翻改成无产阶级性的东西。另一方面,历史学派的思想方式必然引起它的代表人物的保守倾向(这是就“保守”一词的社会意义而不是政治意义来说的),引起他们对于社会的任何彻底改造的厌恶并且使他们把兴趣分散到个别的改良和个别的努力上去。因此,修正主义如果想始终如一地向前发展,也就是说如果想始终有所作为,就必然会同革命的社会主义运动发生冲突。但是,如果修正主义还想继续忠于社会主义,它就会一再被迫面对社会理论的重大问题,并且,只要它不想陷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罗网,不管它是否愿意,便总是要处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因为,如前所述,它找不到另一种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如果谁相信能够提出一个更高的理论,他尽可以干一下。这只有伟大的天才才能做到,——如果做到了,这将是人类智慧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目前还根本看不到这样的伟大天才的萌芽。但是用历史学派的观点既不能修正、也不能发展、也不能铲除马克思主义。事实不是这样简单的。因此修正主义不能从理论上动摇马克思主义,就象机会主义不能从实践上动摇马克思主义一样。修正主义击溃了时髦的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并不为此伤心。相反,战斗着和探索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它的第三次危机中已经光辉地经住了考验,就象在它以前的两次危机中一样。
现在,当我们伟大导师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他对于人类社会,尤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质的阐述,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引导我们前进的北极星,它向我们指明了实现伟大的最终目的,即把无产阶级以及整个人类从资本主义灾难下解放出来的障碍最少的捷径。
译自《新时代》杂志第21年卷(1902—1903年)第1册第723—731页。
译者:辛庚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81年第3期
*本文写于1903年3月,是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二十周年而作。作者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身分谴责了修正主义,但对修正主义的实质和阶级内容作了错误的解释。——译者注(朱老师注:考茨基属于中派社会主义者。)
